【历史文化】“白虎为患”与“刻石盟约”事件‖刘渠
“白虎为患”
与“刻石盟约”事件
刘 渠
战国晚期,巴郡夷人(即后世所称“賨人”)与秦国有一次载入史册的重要的“刻石盟约”。这是一次由“虎患”引起的,用政治手段予以善后处置的事件,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究竟怎么回事呢?
《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1984第1版)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huì),尽搏杀群虎,大吼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盟约,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乃安……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

这段文字,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述略同,仅仅是阆中夷人和“金百镒”有异而已。说明述有所本,是较为可靠的。史料来源大约均取自秦史《世本》所载。
然而,认真审读却甚为困惑:古来虎患何其多也,单单这次虎患显得异常不同;并且,言之凿凿的一次偶发事件,却记录得像一个滑稽的故事,细节经不得推敲,其结局更是匪夷所思。发生“虎患”的时间点,也有那么点“巧妙”。
一、虎患”是一次偶发事件
被记入国史的一次“虎患”,说是“白虎”为首的群虎行动。虎历四郡,害一千二百余人,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若仅仅以“自然灾害”而言,这就是一次偶发事件,实质不在其规模大小。但若以“虎患”隐喻崇拜白虎图腾的廪君巴人所进行的一次武装暴乱,也只能算是一次偶发事件,因为发动暴乱也是有极大风险的,在严重不对等的量级上过招,大概率必然“死得很难看”。不过,失国的廪君蛮上层集团之所以要铤而走险,却是偶然中埋藏着必然因素。为什么呢?这次事件要跟“秦灭巴蜀”这个大事件联系起来看。
原来,末代蜀王讨伐川北苴侯,苴侯是蜀王之弟,先有自立门户之意,早就与迁都于阆中的巴国勾搭在一起。巴子国既与蜀国“世战争”,敌人的敌人就易于成为盟友。被楚国赶跑的极其虚弱的巴国,需要友邦,自然是愿意亲善苴侯的。可是,此时国力很不济,只得求救于秦。秦国君臣早就垂涎巴蜀之富饶,正愁没有向西拓展的适当借口和理由,机会就这样送到了“家门口”。
秦者,“虎狼之国”也。秦国既灭蜀,回头顺手牵羊又取了巴,“执巴子以归”,这是巴国统治集团始料不及的。蜀、巴皆与秦国有正常的邦交,巴人没想到国际间不带“这么玩儿的”,请帮手入境打仗,帮手却将邀约方和所要打击的对手两个一并结果了去。时当战国之际,风云雷电,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最大化,再没有将虚假的道义神圣化。巴国历史上,以巴蔓子将军“一头换三城”的把戏,还算讲“诚信”以弥纷争。是时已今非昔比。

巴蔓子将军像
以此之故,廪君蛮失国贵族心有不甘,仇恨强压在心底,累积着暴乱的能量。仅管秦国相应地采取了降温或预防措施,在政策上表达出笼络的意思,不仅保留了巴人贵族的“君长”名号,并且“世尚秦女”;其民也“爵比不更”。然而,事情却是没完。
二、“白虎”非虎,虎患是一次政治事件
刻石内容与盟约背景这两者不相符合。不难发现这个故事的逻辑悖理。《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记·序》:“……昭襄王时,又有白虎为患,盖廪君之魂也。”前人早就说中了实质。不过,也有学者愣是当作一次自然界的白虎为害故事的。或者据以判断賨人还处于射猎阶段的落后状态,或者因为以“白竹弩”为武器直言还没有进入青铜时代。这两种武断失宜的说法,笔者放在后面讨论一下。
我们且不论射虎之功有如此之大——仅因为“夷人”之嫌而使秦王改变最初封侯的许诺,但除“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的政策性优待外,怎么又将“秦夷互不侵犯”这个与赏赐性质风马牛毫不相干的内容提出并作为盟约的主要条款来了呢?
“虎患”的规模和活动范围。亚洲虎群体活动的少有见闻,尤其是这种异化了的凶猛无比的“白虎”是否能成为群虎之首?令人难以置信(不妨先科普一下。搜狗百科:虎常单独活动,只有在繁殖季节雌雄才在一起生活。每只虎都有自己的领地。尽管虎是独居动物,并有着自己的领地,公虎仍可能常和自己的配偶及孩子们待在一起。成年虎,尤其是同胞兄弟姐妹之间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相互协作,共享收获。华南虎的活动范围大于孟加拉虎而小于东北虎,保守地估计为100平方公里)。从虎的行为特点上看,虎患的规模过大,其活动范围又限于巴蜀、汉中及秦国边境,戕害一千二百人居然没有一个具体细节,史家记事不在情节而重其结果。这就表明其真相并不是一次真正的自然灾害。“白虎为患”就是巴郡内虎巴族人有组织的叛乱和暴动,被另外的一支巴人(后衍称賨人)出兵平息了这次叛乱。而“为盟”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6年前后一年内,因为时当秦国出现王位纷争,这应是“白虎为患”的直接诱因和最佳时机。
“虎患”发生的背景。秦惠文王之子武王(公元前310年—前307年在位)天生神力,争强好胜。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都因此位居高官。他素有问鼎中原之志。其四年(前307年)八月,秦武王与大力士孟说在洛阳周王室的太庙比赛举“龙文赤鼎”,结果两眼出血,胫骨不幸被砸断。到了晚上,气绝而亡,年仅23岁。秦武王无子,何人继位是个“突发状况”。
秦王朝为了继任者的问题发生争执。宣太后想立公子芾,与惠文后想立的公子壮争秦王,并得到丞相樗里疾的支持。但是,赵武灵王却要求秦国迎立在燕国为质的公子稷为秦王。屈从于赵国的压力,最后立公子嬴稷为秦王。秦国群臣大多表示反对立他为君,但在魏冉等人支持下,作为武王同父异母的他,得以继位,是为秦昭王。这时昭王年少,母宣太后听政,以魏冉(宣太后异父长弟)为统兵将军。

沸沸扬扬的秦国王位继承问题终于落幕。但是,这个事态还是天下震动。
在巴蜀,看似天下太平,实则暗流涌动。前有秦武王元年(前310年),蜀相陈庄作乱,杀死蜀侯通国。秦武王派甘茂平定蜀国叛乱,诛杀陈庄。此时,巴郡廪君蛮失国贵族蠢蠢欲动,趁秦国朝政“违和”而发起暴乱,既有前因又当“时机”。
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判定:“白虎”非虎,“白虎为患”就是发生在巴郡的一次政治事件,是巴郡廪君蛮上层集团有组织的一次武装暴乱。史官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乃是王师的“不义之举”带来的后果,不便正面言述罢了。
三、“刻石盟约”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而致强。通过变革土地制度,废除了世卿世禄制;重农抑商,鼓励耕战,依军功授民以爵位;实行郡县制和新的户口政策等,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秦国以“严刑峻法”著称。律法禁私斗及私藏军械武器等等。
面对这次“虎患”,虽有秦王的悬赏,普通民众却是断断不敢以命相博的。历史偶然事件中的另一个必然是,引出了巴郡另外一个族群的闪亮登场,即后来所称的“白虎复夷”或“板楯蛮”出手了。这又是为什么?

板楯蛮天性劲勇,质直尚义,俗喜歌舞。他们擅长制作竹弩,同样具有强大杀伤力,记载“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只是故事情节上的夸张,可以理解为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击毙了暴乱队伍的一些个头目。当然,武器以竹弩为主。这是合法地使用暴力,平息了“虎患”。
这个事件进一步发酵,故事情节又有翻转。说好的赏赐不给也罢了,板楯蛮出手的动机本来就并非稀罕什么重赏。这里边的曲折令人展开更多的想象:比如板楯蛮跟廪君蛮同样严重不睦,历史上他们接壤相处,也是存在领地争夺战事的。因为各自不同族群和地盘,生存空间上的斗争不可避免。宣汉县罗家坝M33号墓主身份显赫,身中数枚箭镞,呈现出其亡于惨烈的战斗场面。然死于哪一次战斗?尘封的往事我们不能据以知悉。

秦国处理平息“虎患”的后续延伸,是整个事件的重点。秦王闻报,当然很高兴了,直接夸赞“功莫大焉”。如果仅仅是射杀了几只虎,三个区区小民虽然有功于国,不予封侯赐爵也就罢了,赏金完全可以且应该给付的。于理不通的是,一次偶发事件完结之后,为什么反过来要与有功人群订立“互不侵犯”的盟约呢?明显是用政治手段来进行善后处置了。讨要封赏的过程被上升到国家与蛮夷关系层面和地方治安稳定的高度,这就摆明“前车之鉴”,需要在国家和蛮夷之间寻求一个维护长治久安的政策举措。当然,缔约对象是基本对等的一方了,即代表整个夷人群体的族酋。秦国约定:对夷人族酋实行“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的优待政策,“伤人者论”是说要看什么情节再计较具体办法,而杀了人却可以“雇死倓钱”,也就是拿钱可以赎死罪。这个尺度大大超越了一般国民待遇。
接着,重点来了——乃刻石盟约,盟曰:
“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互不侵犯条约。违约的质押物品纯粹只是一个象征,体现信守承诺而已,其实质是:
其一,国家实行羁縻政策,板楯蛮享有民族自治地位;
其二,夷人承认秦国的统治地位,遵守国家的基本章法;
其三,秦国对夷人的各项优待政策将长期有效。
这个盟约事实上起到了稳定蛮夷地区社会治安的作用(“夷人乃安”),因而具有重大的政治效应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巴蜀地域上一个崭新开端,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四、“刻石盟约”的历史意义
巴蜀自古为蛮夷所据,国史、方志具载多个蛮邦及二十余种夷人族群或部落,民族关系十分复杂。秦国在新开辟的蛮夷之区,除了建立郡县,推行秦国的政治体制外,在管理民众方面,大体上实行羁縻政策。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分类施治的举措。以巴郡“白虎为患”事件的处置来看,通过“刻石盟约”,可以说成为一个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冲突的经典范例。
以“刻石盟约”事件为标志,巴郡两大族群呈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走向。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笔者注意到这个除去爵位之“罪”不见另载,只是“白虎为患”事件之后,巴氏贵族再无什么大事要闻见于载籍。再后来,说有巴氏五子在枳地又打起了“巴王”旗号,《史记·楚世家》说“楚得枳而国亡”,时间在公元前280年。然后,巴氏五子逃进武陵山,各为一溪之长,是谓“五溪蛮”。而廪君蛮大部分族众东移到了南郡,巴之故国地域,廪君蛮势单力薄,再也没有多大动静了。可见,廪君蛮之罪可能正是“白虎”之乱。
然而,板楯蛮却是异常地活跃了起来。
其一,产生了賨赋之制。赋役制度是集权国家立国的基础,秦国一般国民的“口算”(即所谓“人头税”)为120钱,夷人因为射虎之功,口算仅为一般国民的1/3。谯周《巴记》云:“夷人岁出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夷酋更有“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的豁免政策,的确得到了厚待。
其二,由賨赋而衍生出一个新的族名——賨人。应当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以秦昭襄王时代为分界,以前尚无“賨人”的记载。杨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这是文献中最早记载蜀国之东聚居巴人、賨人的状态。应劭《风俗通义》曰:“巴有賨人,剽勇。高帝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凫乡侯,并复除目所发賨人卢、朴、沓、鄂、度、夕、袭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锐气善舞”。
中原人将巴人归于南蛮系列。所谓“賨”,源于巴人口语。《说文》释賨:“南蛮赋也”;另文释蛮:“南蛮,蛇种”。由此知悉賨人是蛇种南蛮的变名。《晋书·李特载记》说得更明白了:“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可知,纳賨赋这支夷人,原本就是以巨蛇为图腾的巴人。

渠县賨人谷賨王桥(蓬州闲士摄)
賨人之先民是渠江流域的世居土著,大巴山是其发祥之地。“巴”原为蟒蛇,先民族群从新石器时代来到这一地区,在地理认知过程中因为惧怕和敬畏巨蛇,产生集体“崇蛇”的心理意识,遂以巨蛇“巴”成为氏族图腾了。賨人祖先的巨蛇崇拜,已从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渠县城坝2019年发掘M45号大墓,出土三把金剑格的青铜剑,其中一支剑的剑身铸为长蛇覆盖,一支剑的剑身铸有双蛇缠绕覆盖,如此高规格的佩剑,则是墓主人尊贵身份的象征。
其三,“故世号‘白虎复夷’”什么意思呢?古汉语除特定用字外,多有假借或通变。“复”繁体为復,作动词有“覆盖”之义而无“覆灭”之义。“覆”则有“伏击”“覆灭”义项。笔者以为,此处复即通假覆。既然“白虎为患”是故事新编,“白虎复夷”也不便说得那么直白,只可意会。拿现在的话说,“白虎复夷”就是“覆灭白虎的那支夷人”。当然,这个“故世”是指秦及先秦之世。“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既然再无“白虎”为患,何须賨人司以专职?这表明汉高祖对賨人另眼相看,视为“义民”,一依秦时故事,不仅薄赋轻徭,还负责监视廪君蛮不得反叛兴乱,赋予了镇压剿灭“叛乱”的“特权”。
昭襄王后,秦汉宕渠地域中的巴人已演化为“賨人”族称,其人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号。而他们原来的族称则很少有人在意了。
刘邦为汉王时,正如《风俗通》所言,阆中人范目知刘邦必能成帝业,主动要募发賨人参与还定三秦的战事。《华阳国志·巴志》又说:“秦地既定,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我们由此了解到賨人有七大部落,俗称“七姓夷王”。至于“板楯蛮”的名号那就更为响亮了,“板楯蛮”是“賨人”的别称,这是由于后汉时期州郡常率以征伐,賨人所持木盾外形独特,一望便知,朝廷官员或汉人的另外叫法。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卷二说:“板楯蛮以木板为盾,故名。”《后汉书》记载“巴郡南郡蛮”就是以“板楯蛮”为名、从秦昭襄王开始写起的。其后缀是“遂世世服从”,跟《华阳国志》刻石盟约之后,“夷人乃安”各有奥妙。
值得注意的是,盟约中的“清酒”,是一种纯度较高的酒品。《酒赋》谓:“精者为酒,浊者为醴”;《周礼·酒正》:“...…三曰清酒”,是为上品。作为民族争端责任的偿付物品,其名贵程度则“清酒一钟”与“黄龙一双”(金质)等价齐观,成了賨人贵族尊仪和信诺的象征。这一条史料有以下两个信息:
1.这是四川境内所产而见于文献的最古老的优质名酒,距今已2300年以上。酿酒是在谷物剩余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达到名酒还得经过相当长的过程。《华阳国志》记载了賨人世代传唱的歌谣:“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善酿尚饮是賨人社会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四川盆地发达的酒文化也以此为滥觞。
2.表明渠江流域古代农业经济的发达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兴盛。重要的是战国中晚期就有了这样的水平,除地域相对封闭的特殊性所赋予的社会稳定外,以生产力决定论而言,应该是在相当发达的社会组织形态的条件下才有此可能。
此外,从渠江流域罗家坝和城坝发掘的大量战国及更早时期墓葬的青铜器物看,讲板楯蛮尚处于射猎阶段或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断言,已经不攻自破。
五、结语
战国晚期,发生在巴郡的“白虎为患”是一次偶发的政治事件,秦国以政治手段予以善后,反证了事件的性质,不得以自然灾害视之。事件的后续延伸,将这次偶发事件的处置上升到国家与蛮夷的关系和地方治理的高度,遂有“刻石盟约”之举,使之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和处理民族关系的经典范例。它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其目的在于维护秦国新占领的巴蜀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家战略后方的长治久安。秦国总体上对蛮夷之区实行羁縻政策,除建立郡县外,又对蛮夷采取分类施治的政策举措,加之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积极治理措施,确保了巴蜀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汉承秦制,巴蜀地区接续发展繁荣,成为久负盛名的“天府之国”,继续成为大汉帝国开疆拓土的兵粮基地,为推进历史进步和汉民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渠(四川省渠县史志中心工作人员,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特约专家)
配图:方志四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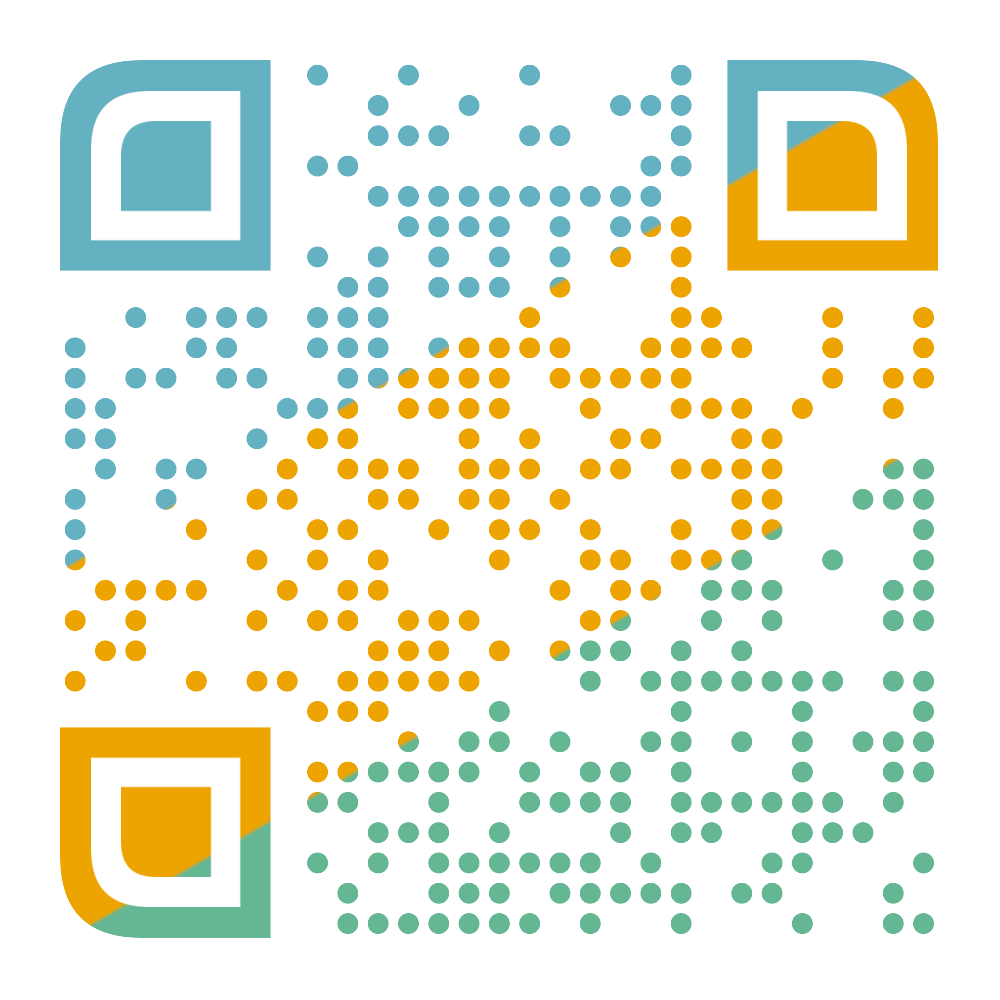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