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 ‖ 山高水长怀伯父——追忆李绍明先生
编者按:2019年8月31日上午,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大学藏学研究中心、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主办的李绍学术思想座谈会在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举行。同时,由著名学者段渝、著名作家王国平主编的《民族花灿忆故人——李绍明先生辞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出版。 今日,方志四川特转载“行脚成都”微信公众号推送 的青年作家王国平撰写的纪念李绍明先生的文章。

2019年8月31日 上午,李 绍明学术思想座谈会在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举行(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李绍明(1933.12.23—2009.8.20),土家族,祖籍四川秀山(今属重庆),民族学家,学术活动家,四川省第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主席,四川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顾问,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原副所长,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研究员。所著《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土家族史》《民族学》《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巴蜀民族史论集》等著作享誉学界。
从1950年进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李绍明就开始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20世纪50年代开始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大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80年代,他主持编写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还编写了《民族学》,这两本书奠定了他在民族学的地位和学术基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被誉为“科学大厦的奠基石”,到现在,《民族学》依然是许多大学的课本。这些年来,他主持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创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主持羌族社会历史调查,合著《羌族史》,为羌学奠定坚实基础。

李绍明(图片来源:行脚成都)

著名学者段渝、著名作家王国平主编的《民族花灿忆故人——李绍明先生辞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图片来源:行脚成都)

2019年8月31日上午,参加李绍明学术思想座谈会的代表合影留念(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山高水长怀伯父
王国平
一
今岁春早,乍暖还寒。
三月的某日,收到吾兄李铣代父李绍明先生转赠的图书《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一册厚达300页的书浓缩了乃父跌宕曲折的一生,留下了费孝通、马长寿、冯汉骥、李安宅、吴泽霖、林耀华、宋蜀华等一个群体厚重无言的剪影。
李铣兄在扉页题字云:“亦先生亦伯父”。
彼时,春风依然料峭,但心中却有暖意升起。诚如斯言,李绍明先生于我,既是关爱之师长,亦是慈祥之伯父。
抚书追昔,墨香扑鼻,偶尔从柔软的时光里抬起头,蓦然惊觉:秋去春来,伯父李绍明先生竟已离去十年。

李绍明(图片来自网络)
二
十年,苍山的云聚了又散。
十年,邛海的月圆了又缺。
十年,格桑的花开了又落。
十年,萝卜的寨毁了又建。
十年,我们在时光里沉睡,又从思念中醒来。

1954年,身着各族服装的研究班学员,二排左二为李绍明 (图片来源: 行脚成都)
三
我第一次见到伯父,是在2005年7月11日。
当时,我参与策划的“大禹文化与江源文明学术研讨会”在都江堰市二王庙宾馆举行,在与会名单中我见到了素所敬仰的著名学者李绍明的名字,内心的喜悦无法描述。因为早在很多年前,我就已读过他的重要著述《羌族史》,由此开始对羌族文化有了初始认知。而他的儿子李铣,则是我多年前就已因诗相交的兄长,因了这一层关系,我对伯父便更有了一份亲近之心。

见到伯父时,一点也没有寻常意义上的意外惊喜,我就像一个内向的晚辈见到了自己尊敬的师长,稍显拘谨。 而伯父却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他一手潇洒地摇着折扇,一手挽着脱下的外套,谈吐之间,风度翩翩,完全是我想象与期待中的大家风范: 温良儒雅、平易近人……后来,当我与他谈起李铣时,伯父毫不迟疑地说: “那你肯定认得到廖永德! 那是个热心人啊……”
多少年过去了,当日的情形宛在眼前。
艳阳之下,树影婆娑,我陪伯父伯母缓步向房间走去,院里洁白的栀子花开得正繁,清香不时袭来,浓郁了那个夏天。
四
以至于我后来在读到李铣兄的诗歌《栀子花》中的那句“依然盛开在往昔的风中”时,总有一种时光倒流、似曾相识的感觉,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下午和穿行在栀子花香中的我们。
疏忽之间,多么像一幅写意的油画,在岁月里慢慢凝固。

2015年,土家族诗人李铣诗集作《月亮上有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诗歌界与评论界广泛关注。2015年4月25日上午,《月亮上有水》首发式在成都大学举行。成都市文联主席朱树喜,成都大学党委副书记宋辉,副校长唐毅谦,成都市文联《成都文艺》杂志编辑部主任、诗人桑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马及时,诗人王国平、马明林、何民、汪浩等参加首发式。图为李铣(站立者)在首发式上讲话(图片来源:四川青少年文艺网)
五
我时常在想,假如许我以更多时光,我多么愿意陪伯父跋涉在祖国的山水之间,在他的身边默默地做一个助手、一个学生甚至一个书童,为他煮茶、担酒、掌灯、抄书……
但是没有假如,所以我只能在往事里遥想伯父的身影。

六
伯父祖籍系原四川省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今重庆市),李家在秀山本是望族,到了伯父父亲李亨这一代开始破落。李亨上过私塾,20岁不到就到酉阳边做杂事边旁听讲学,后结识名人吴嘉谟并随吴到成都做事。吴后任关外学务局总办,李亨亦随之出关,1907年,创办了藏区第一所官办学校——巴塘小学。后来,李亨四处办学,并得到清廷嘉奖,提拔为县丞。清末,同盟会进入巴塘,李亨参加了同盟会,成为藏区早期会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吴嘉谟离开关外学务局回康定,众人便推举李亨代理总办。随后不久,蜀军政府委任李亨为昌都府知事,结果因为当地战事而未能到任。返回成都后开过钱庄、煤矿,经营过百货,搞过交通运输。1927年,四川进入刘文辉时代,刘派李亨担任汉源县县长,李亨在当地为民做了很多实事好事,解决了很多民族问题纠纷,被誉为“草鞋”县长。

辛丑条约及辛亥革命 (局部) 2015年 吴厚信 作(图片来自网络)
1933年12月23日,伯父生于成都,1950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他是教会大学的最后一批学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者;他专攻民族学,也受过历史学的训练;他受西方理念影响,也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熏染;他既是田野工作的践行者,又参与推动了诸多学术机构的创立并担任过领导者。他曾做过费孝通、马长寿等民族学大师的助手,亲身经历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他先后参与少数民族大调查。他著述宏富,在学术界享有巨大声誉和广泛影响,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对藏族社会进行研究,并提出康区的特殊性以及“稳藏必先安康”的重新认识,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肯定;生前曾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民族学科规划组成员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学学会会长、四川省人大常委、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52年8月10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合影,二排居中者为李绍明(图片来源:行脚成都)
伯父是一位道德文章堪称楷模、学术声望名播天下的大学者,他的一生几乎是那一辈中国学人的缩影。他尊重长辈,关爱同仁,提携后学,其治学成就和师表风范,足以成为我之楷模。

1956年,四川民族调查组成员在雷波县与彝族同胞合影,前排右一为李绍明
七
多少年过去了,羌族高山上的羊角花没有忘记。
1951年夏天,黑虎乡的青草才刚刚拔节,伯父就随着老师玉文华先生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少数民族调查。
伯父一行八人,背着口粮和铺盖,从成都出发,向羌族聚居区而去。经过灌县(今都江堰市 ) 时,他们买了豆豉、豆瓣、猪油,用一口大锅把它们混在一起炒好,带着在路上当菜吃。 当时伯父只有17岁,沿途也没有公路,他们沿着岷江河谷遗留的松茂古道,时而翻越高山,时而穿过峡谷,艰难前行,用了7天时间抵达茂县,又走了5天,来到赤不苏区。

松茂古道(图片来自网络)
随后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一行四人挨家挨户地调查羌族政治、经济、生产、人口、文化、婚姻、家庭状况等相关情况。不久又协助地方工作组,推动建立新的基层政权。
据伯父回忆,调查工作非常危险,有一次过一条河,同行的背夫一脚没有踩稳,米就掉下去了,背夫下去检米,结果米没有捡回来,人却被冲走了。背夫被冲走,大家心惊胆战,但自己还得过河。最后不得已,决定女同学走上游,男同学走下游,一旦女同学发生意外,方便救援。结果女生张亚庆一不小心跌入水中,幸得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性命。

1951年,前往茂县黑虎乡调查途中,后排右一为李绍明(图片来源:行脚成都)
乡政府成立时要选举领导,投票效仿解放区的做法,被选举的人坐着,每个人背后放一个碗,选举者想选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投一个豆子,这个乡政府就称为“豆选乡”。
后来,伯父又多次前往羌族聚居区调研考察,1985年,他和冉光荣、周锡银合著的《羌族史》正式出版,为羌学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成为羌族研究领域极其重要的学术著作。

1982年“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全体人员在四川渡口市(今攀枝花市)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位戴眼镜微胖者为李绍明先生,前排左起第九位是著名的考古学家、科幻文学家童恩正先生,童先生旁边双手扶膝者是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汪宁生先生(图片来源:行脚成都)
八
多少年过去了,大小凉山上的索玛花没有忘记。
1952年,伯父随川南民族访问团一行前往小凉山、峨边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当时国民党特务控制了峨边县的西河地区,伯父们不仅要做民族调查,同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在特务、土匪的密切关注下,积极劝说和争取彝族上层人士,靠拢政府,一个多月的调查,让他对彝族有了崭新的认识。
据伯父讲,当时彝族地区盛行买卖奴隶,一个黒彝奴隶主居然看上了访问团的两位女团员,想用钱来买她们。伯父当时就开玩笑问:“怎么个买法”,黑彝奴隶主给出的价格是胖点的女团员50两银子,瘦点的女团员40两银子。
1956年至196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进行科学调查。此活动由毛泽东倡议、彭真负责。调查工作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持,成立了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刘格平、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组成的调查领导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少数民族的《简史》,为我国少数民族名称确认和民族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1956年,李绍明在凉山社会历史调查组时期的戎装照(图片来源:行脚成都)
伯父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实践活动,万万不能错过,于是他通过多种渠道争取到了名额。1956年10月1日,伯父随四川民族社会调查组前往凉山,参加了布拖县则诺乡(黑彝统治腹心区)、雷波县马颈子乡(黑彝边缘区)、雷波县土坝乡(独立白彝地区)、甘洛玉田乡(土司统治区)。伯父和同事们一起,白天走家串户做调查,晚上还必须将调查资料赶紧整理出来,调查时间长达一年多。
第一阶段调查结束后,凉山发生了武装叛乱,调查组再次开赴凉山调查。 为了保证调查人员安全,伯父等接受了军事训练,人人配枪出门调查。 当时,为了解决民主改革中的叛乱平息问题,专门成立了中央慰问团,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委主任王维舟任团长,四川调查组夏康农任副团长,夏先生让伯父做他的秘书,从调查组借调到慰问团工作。

1949年11月由陕入川解放大西南时,贺龙、周士第(右二)、王维舟(右一)同志在进军途中(图片来源:汉中档案信息网)
伯父回忆,1956年底的一天,他带上一个武警,去布拖乡下了解一个奴隶主的情况,本来是准备当天返回城里的,后来因事耽搁,当天没有回城。后来才知道,当天叛乱分子就埋伏在他们回去必经的一个山垭口,等着收拾他们。要是当天赶着回去的话,可能已经没命了,想起都后怕。
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调查工作依然坚持开展,伯父忆及此事时说:“本来凉山奴隶制度解剖一两只麻雀就可以了,但我们解剖了十几个麻雀,前前后后那么长时间,花了那么大力量,就是为了要最终确定凉山的社会性质。”
最终,依据凉山彝族的等级关系、阶级关系、土地制度和剥削方式,证明当时的凉山就是奴隶制社会。1982年,由伯父担任总篆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凉山彝族社会的著作。该书对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作了介绍和分析,同时还对彝族的来源和它经历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该书被学界誉为“科学大厦的奠基石”。

1998年6月,李绍明与李铣摄于成都土桥(图片来源:行脚成都)
九
多少年过去了,阿坝高原的格桑花没有忘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阿坝州民族教育非常落后,仅有一个民族干部训练班。1954年,伯父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受命和其他人一起前往阿坝,创办阿坝州民族干部学校。
学校原在茂县,后迁薛城,最后迁到刷经寺,伯父去后,负责学校的教育科工作,同时教授《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学校创办之初,从各个地方招收学员,学制一年,学校定位是为新生的阿坝州培养区、乡一级民族工作干部。
在阿坝工作期间,虽然曾被错误地列为肃反对象,但是伯父依然对那一段时光充满感情。他曾讲到,当时的学员主要是藏、羌两族,也有少量回族和汉族,人数达到200多人。学校虽然搬迁多次,但是当时的教学环境始终没有得到改善,极其简陋。当时薛城旁边有个川主庙,大殿可以容纳几百人,学校就将大殿改做礼堂,200多学员在那里一起上大课。
因为学员来自不同民族,很多学员不懂汉语,上课必须要三个翻译,一个嘉绒藏语翻译,一个安多藏语翻译,一个黑水话(羌语北部方言)翻译。因此当时一个课时虽然有一个小时,实际上只能讲半个小时,因为翻译就要占用一半时间。一般是伯父先用汉语讲课,会羌语南部方言的学员懂汉语就不用翻译了,其余三组学员各围成一个圈,中间坐一个翻译,伯父讲完之后,听懂了的人就在旁边等着,教室里啊嗡嗡嗡的声音四起,等其他三组翻译完之后,才能继续讲课。
教学之余,伯父依然没有放弃在学校附近做民族调查,远到蒲溪沟、杂谷脑,近到大岐山、小岐山、九子屯,许多山寨都留下了伯父骑着自行车或步行的身影。 学校创办后,培养了大批民族工作干部,他们就像撒在阿坝州的一粒粒革命的种子,他们把知识带进了当时还显落后的山区,为阿坝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伯父还与许多学员成了好朋友,几十年来,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1957年秋,四川民族调查组在灌县(今都江堰市)合影,右二为马长寿,右四为李绍明(图片来源:行脚成都)
十
伯父不仅重视社会实践与民族调查,同时也始终关注和积极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利用五七干校设在民族杂居区的条件,在节假日进行调查访问。1977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恢复,他回到自己热爱的研究领域,全面整理过去的成果,进行理论升华。
1980年,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前身中国民族研究会成立,伯父先任理事,后任几届副会长,期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积极支持时任会长秋浦和宋蜀华先生的工作。同年,伯父在四川大学,将中断了很多年的民族学捡了起来,重新开课,后来童恩正、程贤敏又先后开讲文化人类学。为了建立民族学学科,伯父将讲稿作了理论提升,撰成《民族学》一书,中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多所大学将其作为本科教材,在民族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为推动西南地区的民族学科建设,伯父从1978年就开始思考怎样整合与优化西南民族学研究资源,推动西南地区民族学发展。1980年,伯父联络了云南的何耀华、贵州的余宏模、广西的李干芬和周光大等人,成立了筹备组。1981年,在伯父等人的奔走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正式成立,伯父作为秘书长,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推动学会工作。学会成立迄今已有37年,举办过20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出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集刊》多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伯父与何耀华、童恩正主持了“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随后,伯父等又致力于“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得到了费孝通先生的大力支持。同时,伯父还主持了酉水流域土家族调查、西南丝绸之路调查、金沙江流域考古文化调查等、“康巴学”研究,均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5·12”汶川大地震后,伯父又致力于羌族文化抢救与保护,即使在病床上,伯父也念念不忘那个云朵上的民族。

2004年5月9日,李绍明率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研究课题组搭乘农民的运输三轮上仇池山考察(图片来源: 行脚成都)
十一
遗憾的是,我与伯父相识恨晚,加之生性懒散,虽然相见不少,却没有珍惜向伯父学习与请教的机会,虚度了很多光阴,但是伯父对我的鼓励和扶持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8年4月8日,都江堰市举行我的新书《都江堰——两个世纪的影像记录》作品研讨会,邀请的嘉宾名单中,当然有伯父。我向伯父送请柬时,他抱歉地说:“小王,书看了,非常好,现在没有几个人愿意做这个事了。真的很遗憾啊,我要去参加湖北的一个学术会议,来不了啰。”伯父又说:“我这里有一批灵岩山的老照片,是加拿大人在1940年代拍摄的,很珍贵,我资料太多,找到后交给你。”

告别时,我很 失落,伯母悄悄跟我说,伯父为了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专门向学术会议主办方请了半天假,但是因为时间紧迫改签不了机票,不然定会参加我的研讨会。 伯母的一席话,让我心中的失落一扫而空,满满的都是感激之情。
也是在当年,因为我拟申报成都市有突出贡献专家,需请四位专家推荐,我立即想到了伯父、谭继和先生、张新泉先生和意西泽仁先生。我与伯父电话说明了此事,伯父欣然答应。4月25日晚,我匆匆赶到伯父位于民研所的家中,他则已等候多时,并已提前写好了草稿。伯父说:“时间过得好快啊!十多年前,我还给谭继和先生写过推荐意见,没想到,转眼之间,就已轮到你们这一批年轻人了。”
随后伯父在推荐表格上认真地写下了推荐意见:“王国平业绩突出,思想敏锐,长期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的创作和研究,成绩显著,成果丰富,是难得的青年学者型作家人才。”
鼓励与褒奖之意,溢于笔墨之间。
临走时,伯父送我到门口,拉着我的手说:“小王,好好干,我们的事业需要你这样认真好学的年轻人。”昏黄的路灯下,春风透着凉意,吹乱了伯父额前花白的头发,但他镜片后的眼神里却满含着希翼与期待。
我心激动,紧紧握住他手,说了声“谢谢!”

2005年5月20日,李绍明、林向考察水富张滩坝墓葬发掘(李星星 供图)
十二
2009年5月,我与殷波合著的《现在的我们——“5·12”都江堰大地震幸存者口述》出版,我以为这是一本最接近地震原貌、很有意思的书,非常想送一本给伯父,请他批评。

然而,我连续三天拨打伯父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 最后,我实在放心不下,就给李铣兄去了电话。 听筒对方的李铣兄声音憔悴而伤感,他说: “父亲住在三医院,这次病情很严重! ”
我难以相信,因为半年前见到伯父时,他还精神抖擞。我匆匆赶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伯父神形憔悴,不过精神不错,谈兴很浓。听说我出了一本口述史,伯父异常兴奋,蜡黄的脸上泛着喜悦的光泽,他说现在看书不便,想听我讲讲。于是我强打起笑脸,与伯父谈起了我们采访的幸存者在“5·12”大地震中惊心动魄的逃生经历。特别是讲到地震前一秒,一位练气功的老太太正怀抱太极,往外一推,墙就倒了,老太太以为自己练功几十年,终于圆满了,于是欣喜地大叫一声“儿子,大功告成!”时,伯父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个口述史做得好,地震中的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灾难样本,它具有多重价值!我要建议羌族地区也要做一部口述史,对很多历史文化进行抢救式保存。”临走时,我本不想留下带来的图书,伯父却说:“放在这儿,我慢慢看。”

2004年5月14日,在甘肃天水麦积山摩崖石刻参观,从左至右为:李星星、段渝、李绍明、陈剑、石硕 (图片来源: 行脚成都)
十三
然而,我依然低估了伯父的病情。
当李铣兄告诉我伯父已是肝癌晚期时,我一下子懵了。
我记起了冯广宏先生曾经给我讲过的一件事。多年前,伯父曾受邀去韩国讲学,临走时,韩国总统问他有什么愿望,伯父说:“我想见见你们国家的萨满。”萨满是对北亚萨满教中高级神职人员的尊称,当时韩国总统聘请有不少萨满,于是便安排了编号为4的萨满与伯父见面,但是见面时有一个要求,萨满只会谈两个问题,伯父只能问一个问题。萨满说的两件事是:一、伯父的学问来自母亲的教育;二、伯母此时正在生病,伯父回国后,自然会好,此事后来应验。伯父问了一个问题:自己能活多少岁?萨满告诉伯父,以伯父的身体状态,应该可以活到80岁。
而伯父,辞世那一年才刚刚76岁啊。
对一个学者来说,正是他的白银时代。

2005年8月17日,李绍明先生回到出生地:汉源县清溪镇文庙 (图片来源: 行脚成都)
十四
伯父去世后,我读到了上百份唁电、悼词和纪念文章,作者既有中央、省、市各级领导,又有民族地区的兄弟姐妹,更有广大学界的学术同仁,文字里既有对他道德文章的尊崇,也有对他学术成就的敬仰,更有对他人格魅力的钦羡。
从那些温暖的文字里,我又再次认识了伯父。

2007年9月20日,李绍明在西宁“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两岸学术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 (图片来源: 行脚成都)
十五
伯父的足迹曾踏遍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山山水水,山水间,每个民族都是祖国大花园中的一朵灿烂之花。
而沿途的每一朵花开,都是一次深情的忆念。

格桑花(蓬州闲士 摄)
作者简介

王国平,1976年生,四川江油人。70后代表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全省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芙蓉锦江》副主编,《都江堰文学》执行主编。
著有人文地理随笔集《都江堰:两个世纪的影像记录》,大型访谈录《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诗集《挽歌与颂辞》《琴歌》等。其中,《南怀瑾的最后100天》连续5周蝉联当当网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冠军,荣登中国北京书市销量榜首,与《之江新语》等一起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畅销书。曾参加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第九届中韩作家会议。作品曾入选《中国诗歌精选》《中国最佳诗歌》等选本及“5·12”大地震诗歌纪念墙。作品曾入围全国鲁迅文学奖,荣获第十一届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四川文学奖,第十六次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都市人民政府第六届金芙蓉文学奖,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九、十次哲学社会科学奖,成都市委第六、七、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等。2012年6月,应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之邀,赴太湖大学堂为南先生做口述历史。
(注:“编者按”中李绍明及文后王国平简介资料,分别来自2009年8月21日《华西都市报》及中国诗歌网)
来源:行脚成都
作者:王国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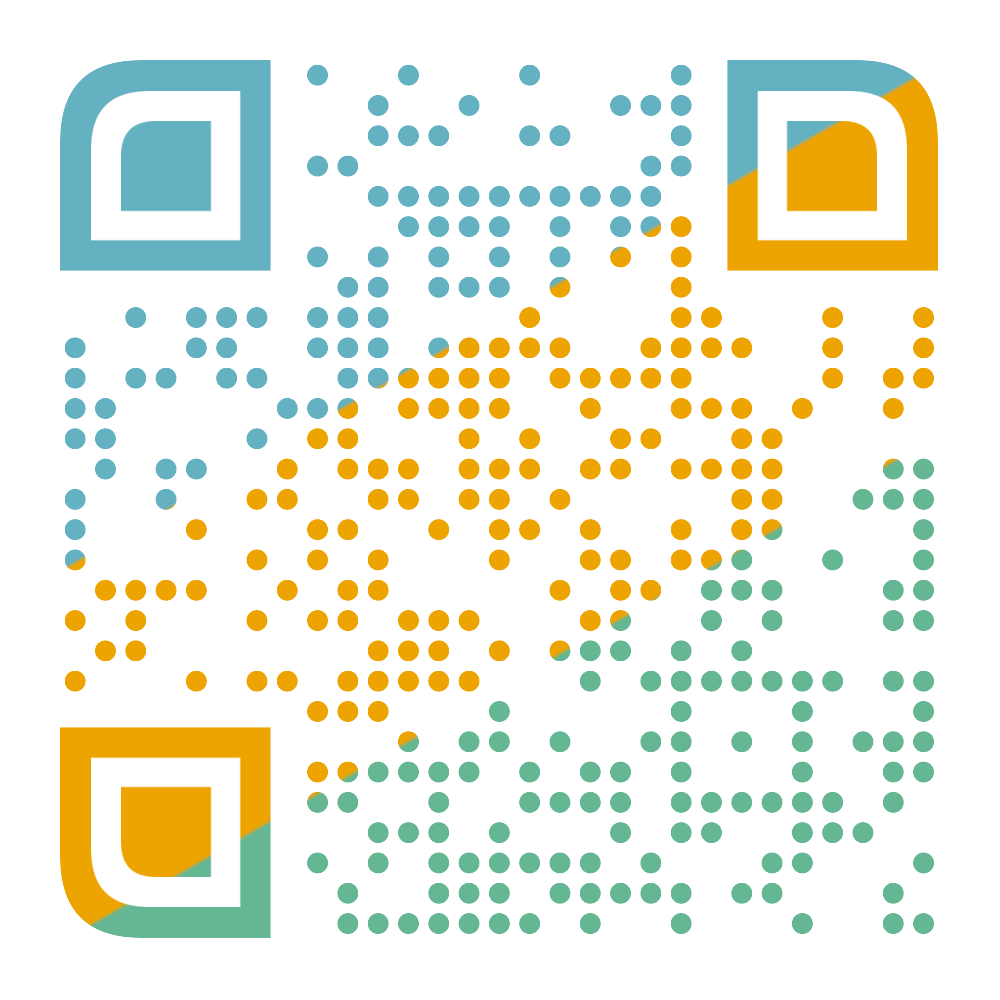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